|
全钢无边防静电地板 http://www.smdiban.net/chanpin/chanpin272.html 我的边防我的连 辛荣祯 第一章:“雪海孤岛”红山嘴 第二章:会挽雕弓如满月
第六节:盘点学习:这里比赶超的氛围一直很浓 说到学习,就不得不说到巴克图会谈会晤站。 巴克图会谈会晤站和巴克图边防连只隔一条马路。 第一次到巴克图会谈会晤站是在10年前。说来也是巧缘,那次是为了编辑《塔城边防军旅文丛》,这次写巴克图会谈会晤站的故事,是因为《我为祖国守边疆》这套文丛。 原分区政治部主任魏怀润任职期间,为塔城军分区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学人才,几年来,文学创作高潮迭起,成果丰硕。为了总结和回顾文学成就,开辟更为广阔的文学大田,他决定汇总编辑一部边防军旅文学丛书。再三权衡,编辑部设在巴克图会谈会晤站。用魏主任的话来说,那里环境好,学习氛围浓,文气旺。 会晤站离市区十八公里,我们坐三菱车不到一刻钟就到了。 没想到时光明站长早已等候在大门口,我们受宠若惊,一个个从车中跳下来,上前和他握手。 时站长是标准的军事指挥官,脸膛棱角分明,腰板坚挺笔直。他原是守备十二团司令部参谋,一九八八年部队整编,该团撤编,被分流到边防S团,先后任团军务股长、步兵营营长、团参谋长,后到会晤站任站长。 会晤站长虽是正团职编制,但只管一个班的人。作为曾任团参谋长的时明光其失落之感,可想而知。然而,他并未消沉,在带领全体人员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,大抓干部战士的学习,很快掀起了文化学习热潮,在短短两年时间内,先后有三人取得了自学本科的学历,五人取得了自学大专的学历。他带领全站人员在“建设学习型机关”中走在了全分区前列。 会晤站环境幽雅,富有诗情画意。办公楼前有两块草坪,草坪有十棵橡树,高大入云,很是壮观。最有趣的是穿过办公楼右侧偏门,向前大约五十米处有一个水塘。水塘四周芦苇茂密,水鸟不时从苇中窜出,让初来乍到者大吃一惊。靠水塘右泊一小船,可顺木桥下至船中,撑着船,拿着网,到塘中捕鱼。塘中鱼是从额敏河捕来的金黄背鲤鱼,味道鲜美。但凡有客来,管理员孙存久都要亲自撑了船到塘中去捕几尾,炊事员做成红烧鲤鱼,招待来客,这是会晤站的一道特色菜。 我们被安排在会晤站招待室。简单收拾一下,就开始工作。魏主任再三强调要快速度、严要求、高质量,所以我们也马虎不得,加班加点地干了起来。 会晤站有间二百多平方的文化活动室,里面有台球、乒乓球、象棋,还有健身器材。每天晚饭后,我们几个都要到活动室活动半个多小时,消解一天的疲劳。我比较擅长乒乓球,经常和时站长对决。时站长是体育全能,各类球都会打,而且打得不错。他的乒乓球打得准、稳、狠,我十有八九都要输给他,但跟高手过招,能够学到真本事,一月下来,我的球技提高不少,这大概是那次编稿之余的意外收获吧。最有意义的是每到周五下午,我们几个加入会晤站业余篮球队,前往对门的巴友图边防连,进行篮球赛。以往因为会晤站人少,只有五个篮球队员,比赛时全得上场,而连队人多球员多,他们轮番上阵,会晤站几乎就没赢过。自从我们加盟后,会晤站势力大增,几场球赛下来,连队全输了。时站长大喜,每次打球回来,都要通知炊事班加几个菜,以示犒劳。 秋高气爽,景色宜人,心情自然舒畅得如同到了世外桃园。然而好景不长,过了十多天,气温骤降,老天的脸色很不好看了。招待室本来建在背阴处,天气一变,住在里面如同冰窖一般。不好,我们五人中有三人已被冻感冒了。 张军翻译给我们送来了两件大衣,这无疑是雪中送炭。 张军,甘肃武威人,憨直,热心,好学,是边防部队翻译界的佼佼者。因为我和张军在边防S团政治处一起共过事,同时又在一个宿舍住过半年,所以我们比较熟,无话不谈。 “听说你们站的刘彦超编了一本书?有这事吗?”一天,我和张军闲聊,随口问道。 “他编写了一本《边防会谈会晤常用语俄汉词典》,用了三年多时间,呕心沥血,不容易啊。那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,常看见他宿舍的灯亮着。”张军深有感触地说。 “哦,是这样吗?”我一直认为编写词典之类的是专家教授的事,好像与实际工作者无关。“书店里像这样的词典不是很多吗?为什么还要费心劳力?是不是有点沽名钓誉之嫌?” 张军一笑,说:“话不能这样说,你没参加过实际的翻译工作,你不了解情况。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,它是随着时代和生活在不断发展变化的,尤其到了信息时代,语言的变化速度更快了。而相对来说,词典的更新速度远远地落后语言的更新速度。像书店的的词典都是十几年前的,有的甚至是几十年前的,根本无法适应现在实际工作需要。所以,要做好实际翻译,尤其是做好两国会晤时的现场翻译工作,必须要及时地搜集整理新词新语,做到有备无患。” 听了张军的一席话,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,说:“有道理。”为了掩饰我的尴尬,我又找了一个话题:“听时站长说,你经常一个人用俄语演话剧?” 张军倒不好意思了,他摸了一下头,说:“时站长在开我玩笑呢。其实我是在用这种方式练习翻译呢。通过现场场景的设置和推演,随机做好翻译,这样学得快,而且到时不怯场,一举两得。你一直搞干部工作的,我的情况你很清楚,我当时学的是俄语翻译专业,可是大学毕业后,撂下好几年了,得补啊。” 张军是地方大学生,一九九五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系,学的是俄语专业。俄语当时属冷门,临近毕业,张军正为就业问题犯愁。但憨人有憨福,当时军队正要从地方大学招一批学有所长的应届毕业生。张军正好赶上了这个好机遇,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跨入军队的大门,一进大门就挂上了中尉的军衔。但是,张军一到边防S团报到后,他摊上了犯难的事。团领导为了充分锻炼他,让他到连队去当排长。他的兵龄才有半年(部队招入后,在西安陆军学院集训了半年),怎么带兵,心里确实没谱。还好,不久政治处又调他到组织股当干事。说心里话,这个比当排长还让他犯难。组织股的材料多得像牛身上的毛,之前他根本没接触过这些,一切都得从头学起。自从踏进组织股大门,他三个月几乎没有回过宿舍。在组织股长冯满仓的指导和帮助下,张军慢慢地进入了情况,一年后,他和另外一位大学生干部张长城成了政治处的两大笔杆子。一晃四年过去了。由于巴克图会谈会晤站的几位翻译先后转业,翻译力量极其薄弱。为了补充力量,正在政治处干得风生水起的张军被调到了会晤站。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这下张军又犯难了。他拿起俄文资料一看,满眼生疏。虽然业务丢下了四年,但毕竟是专业对了口,他信心满满,一切从头开始。他每天早上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,围着芦苇塘背记单词、练习口语;每天晚上比别人晚睡一个小时,在学习室里查阅词典和相关资料。暑去寒来,不到半年时间,他完全熟悉了以往所有学的俄语知识,很快适应了翻译工作。 “你们会晤站是分区树立的学习典型,你能详细说说吗?”看到张军谈兴正浓,我顺藤摸瓜,想从他口里探出点实情来。 张军嘿嘿一笑,说:“我们会晤站的学习氛围没得说。这里虽说是个小单位,但学习的热乎劲比大学院校还要强。就拿我们前任站长崇祥庭来说,他以前是边防S团的副团长,军事领导干部,带兵练兵的,但到了会晤站,他不但带头学习俄语,还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研究生班的学习,转业前他拿到了全国级的律师资格证书。现在的时站长,学习劲头更足,他报了法律自学考试本科班,平时还学俄语、练书法,成天比我们还忙。管理员孙存久,司务长出身,以前学的是财会专业,不但本职业务精通,到会晤后,每天坚持自学俄语,两年后,能熟练用俄语对话,这不前几年翻译少,有时忙不过来,他就顶替翻译上阵,任务完成得很出色。” 学习促进翻译,翻译促进学习。这大概是巴克图会谈会晤站创建“学习型”集体的动因吧。 中哈划定边界后,边防执勤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,双方会谈会晤工作随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。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,作为参加了120多次会晤的资深翻译张军谈了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—— 过去双方可以说是“各扫门前雪”,各自负责自己防区的事,很少管对方防区的事。不仅如此,还由于“争议地区”问题的存在,双方还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摩擦和不愉快。现在完全不一样了,可以说是“像亲戚一样,越走越亲了”。从二〇〇九年起,双方开展“肩并肩、手拉手”联合管控边境行动,每月组织双方成员和执勤组,对重点地段实施联合管控,探索了“联合巡逻、联合搜索、联合演练、联合抓捕”的行动模式。这几来,双方还互相邀请对方官兵参观哨所,切磋执勤技能,观摩封控演练,交流边境管控经验做法,有效提高了边防管控能力。 过去双方多数是一些“程序性”的活动,而现在都是“实质性”的行动,用时站长的话来说就是“不向对方挑毛病,多为对方解难事”。中哈双方官兵就像兄弟一样,彼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一次,在北山方向,对方接到了牧民丢失了三十七匹马的报告,便通过会谈会晤请求我方协助查找。分区派人寻找了十几天,最后找到了马群,马上约请哈方现地会晤,当面进行移交。面对失而复得的马群,对方代表助理哈力克发现多了一匹马,以为中方弄错了,执意要退还一匹。时站长解释,这期间一匹母马产下了小马驹,所以就成了三十八匹,我们必须一同移交给你们。对方听后,竖起大拇指,连声赞道:中国军人的,这个样子的!
(注: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) 作者简介: 辛荣祯军旅作家,1975年生于甘肃秦安,毕业于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,现为新疆作家协会会员,先后发表文学作品300余篇(首),曾获兰州军区“昆仑文艺奖”,出版有诗集《山月》、长篇小说《红柳河》、文学评论集《耕雨斋诗话》等。
作者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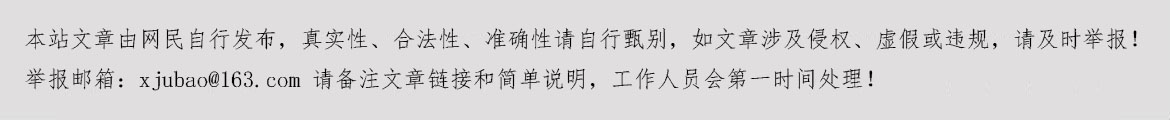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