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年年有今日 https://www.touzitop.com/ysjd/11611.html “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,有多方面原因,主要是随着教育程度提升带来的挣钱能力的提高,从而在家庭经济收入中贡献更大,才获得更多关注和尊重。这样来讲,其实她们在依赖于男方的同时,也依赖于自我。” “那些留在农村的同龄女性,在想些什么,做些什么?” 2018年秋天,刚刚入读复旦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的宓淑贤,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下辖的一个村子里,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。 宓淑贤就在这个村子里长大。开始读博时,她就开始思考自己的博士论文要做什么。她想到,许多社会人类学家的著作,其实正是从自己的家乡做起。于是,她回到家乡,在不同的仪式现场,婚礼、葬礼、宴席上,用人类学的视角观察,和村里人聊天,慢慢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。 在一个葬礼上,宓淑贤发现,在仪式上抛头露面都是男性,她和这些男性聊天,对方总是“端着”,或者敷衍而过。她觉得,这也许因为自己“是一个小辈”。随后她进一步发现,仪式结束后,有些女性聚在一起,磕头、哭丧。其中一些,正是她从小就认识的朋友和长辈。而她和这些女性更能聊到一起。 与宓淑贤不同,这些与她同龄的女性选择了留在农村,留在“乡土社会”里。她们的生命体验,和宓淑贤截然不同。随着调研深入,宓淑贤把研究对象确定为1985年至1995年间出生的“新生代农村女性”。在博士论文里,她写下不同的农村女性,在娘家和婆家的不同生活状态,从而对比在不同角色之下,女性如何受代际关系影响。 如今,宓淑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,即将赴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任教。7月份,全现在和她进行了一次对话,聊了聊她笔下的“新生代农村女性”。 完成“基本家庭责任”后,才被容许追求个人欲望 全现在:长大后再回来,觉得和你小时候相比,家乡发生了哪些变化? 宓淑贤:方方面面都有。我从高中开始去县里上学。后面虽然每年有假期就回家,但感觉和家乡成了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我在调研的时候,直观而深刻的体验是,现在这个村子,已经和我上高中之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,不管是生活经历还是体验,都完全不同了。 差不多十年前,我们那个村子的女性还是留在家里面的,通婚也是和周边的村子。这十年间,很多女性选择嫁到外地,或者很早就出去打工,留下的女性很少。我觉得这部分女性是值得关注的。那些走出去的部分当然也值得关注,但是因为流动性比较强,很难在短时间内把握她们整个群体的特点。所以最后聚焦在了留在农村的女性。 我后来主要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,比如说看村子里仪式的变化、家庭关系的变化。 刚开始研究的时候,我想先去一些仪式活动,去人群中,看大家在聊什么、关注什么。进入某些家庭,通过聊天的方式参与观察,看看农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。 能观察到的是丧礼的仪式不一样了——这个也和政策有关,前几年有个领导的想法是让丧葬仪式精简化。2018年的时候,丧礼上还会有专门的团队吹唢呐,唱曲,晚上表演小节目。现在这些都没有了。但丧礼不可能是安安静静的,办丧礼的人就会租赁一些音响,来放哀乐。2019年,我参加的另一场葬礼上,有人搞了一个大电子屏,播放一些哭丧的视频,有两个人唱曲,感恩母亲的养育之恩,说母亲去世怎么怎么让人痛苦。 晚上的活动也变了。我小的时候,农村的女性到了晚上,就是在家里带娃、洗洗涮涮、织织毛衣、补补袜子。但现在,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晚上都会出去跳广场舞。另外就是老生常谈的,电子设备普及之后,每个人都在刷快手、抖音,还有火山小视频。 还有就是,婚姻的不稳定性变强了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有一天晚上我去跳广场舞的人群里观察。遇到一个小朋友,是奶奶带过来的。奶奶在跳舞,她就在旁边玩。我去跟她聊天,聊着聊着,她告诉我说自己有两个爸爸。后来我知道,是她妈妈离婚之后再嫁了。另一个小姑娘也说,班上还有其他同学有两个爸爸。这些小朋友觉得这不是多大的事情。这在十年前是完全不敢想的。 宓淑贤在田野调查期间所观察到的一场葬礼。图片:受访者提供 全现在:你和不同的人聊了这么多,聊到的内容应该是非常繁杂的。后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向代际关系这个主题的? 宓淑贤:我最初听到农村有这么多广场舞队伍,而且延续这么久,第一反应是,这是一种觉醒吗?因为在我的童年里,女性是要留在家里照顾家庭的,所以现在她们不用管这些了?这是我的疑问。 于是我在不同的场景中和人们聊天,发现大家在谈论到个人的时候,都会聊到自己和他人的关系。比如我问一些女性,你们晚上为什么出来跳舞?有人就说我晚上没事,我孩子去上辅导班了。有人说,我跳舞可以锻炼身体,可以减肥,这样我老公会喜欢。还有人说,我陪我小婶子一起来。 我就觉得,这些女性和以前不一样的。我父母那一代人,可能穿得邋里邋遢的,觉得钱要省下来给家人用。当这一代人开始关注自我的时候,她们有空闲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,其实说来说去说的还是和别人的关系。我们认为个体的东西,其实还是亲人在推动着她们生活的决策,不管是上一代还是下一代。 广场舞中,那些年纪大的女性为什么也去呢?就是她的孙子已经比较大了,不需要她怎么带了,她才出来,她儿媳妇甚至支持她出来活动。这些去追求自己个人欲望的农村女性,其实都是完成了她所属的乡土社会所认定给她的一些基本家庭责任。这些没有写进法律里,但是和社会结构、村落的整体状况,以及年轻人的现状都有关系。 所以我最后确定的主题是代际关系对新生代农村女性的影响。 全现在:你论文摘要里也有提到这点,说“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完成家庭基本责任后,才会被容忍满足个体的欲望,这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个体主义,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主义,而是一种更具有包容度的中国式个体主义。”其后,你又说:“新生代农村女性已经不再附属于男性家庭成员,而是与之相互依赖。”这句话怎么解释? 宓淑贤:就是说,她们追求个体的欲望的时候,不是完全抛开男性家庭成员不管,也无法抛开。不管是和自己的子女,还是和公公婆婆。这些代际关系都是因丈夫的存在带来的,她们无法避开。 相互依赖有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。新生代农村女性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,挣钱能力提高了,在经济上不是完全靠男方家庭补贴了。精神层面的话,有这样一个例子。 我的田野中,有一个男性,现在应该四十五六岁的样子。他以前的经济条件比较差,长相也普通,不太好找媳妇。二十七八岁的时候结婚了,但妻子后来觉得他不够浪漫,跟别人走了,留下一儿一女,但没离婚。后来她跟后一个男人关系不好,就又回去了。这个男的也没说什么,还是一起生活。没多久,妻子觉得他挣钱太少,又走了。 再后来,这个男的搞了一个建筑队,当上了工头,赚到了钱。于是媒婆上门了,介绍了一个二婚的女性,带了个十来岁的儿子。外人就觉得对这个男的来说不合算,因为他们结婚之后,他还要负责继子的婚姻,承担更多经济成本。但在我的访谈中,这个男的自己觉得(这桩婚事)是合算的。因为他的经济地位起来了,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,这样挣钱才有奔头。这次婚姻里,他变得更想和妻子有精神上的共鸣。所以他不太在意这些外在的条件了,而是在精神上和妻子产生依赖。 在传统社会甚至在更前的社会,像费孝通先生做田野调查的时候,结婚就是过日子,男的找一个女的生儿育女,这才是婚姻的本质。婚姻一开始就不是基于感情的,而是一个经济单位。费孝通先生做研究的那个时期,上世纪30年代,农村夫妻之间极少交流,要相敬如宾,说太多话就会吵架。 而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升,有多方面原因,主要是随着教育程度提升带来的挣钱能力的提高,从而在家庭经济收入中贡献更大,才获得更多关注和尊重。这样来讲,其实她们在依赖于男方的同时,也依赖于自我。 宓淑贤参与观察的一场广场舞。图片:受访者提供 “在农村,人们相信的是眼睛看到的东西” 全现在:你在论文里提到,在你的田野点里,新生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是最近才发生的变化。 宓淑贤:通过受教育来改变命运,这个观念在农村不是一下子形成的。 我们那个村子分成东西两边。东边大多数人初中没读完就辍学,出去打工挣钱,一家几口人都打工,然后回家盖房子娶媳妇,人生好像很圆满。西边则是,孩子都被送去读书,考不上高中就花钱上。他们前期过得很辛苦,但只要把孩子送出去的,后来都在外地安家了,过得也不错。 后来东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况,就觉得,我们没有上学,挣的都是辛苦钱,所以上学还是好的。所以这个村庄的风气是慢慢形成的。在农村,人们相信的是眼睛看到的东西。当他们看到这个东西真的有用的时候,才愿意有这样的改变。 我想起一个案例,村子里有一位女性,我们叫她A女孩吧。她40多岁了,她的父亲最开始不想让她上学。但她当时考上了一个中专技校,本来毕业之后可以到一个还可以的工厂上班。 A女孩还有两个同学,三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。A的分数最高,B和C都比她低一些。B的父母同意她去读书,后来B就去了昆山打工,嫁给了一个当地人,现在生活比较富足。C也差不多。对B和C的家庭来说,其实教育程度成了婚姻中的一种议价因子。 但A最后留在了老家。她父亲也没有说不让她上学,他就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说:你哪个叔叔哪个伯伯欠我们家的钱,你去找他要,要到钱之后你就可以去上学。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,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事?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,她也没有读成书。后来她在农村出嫁,再离婚,现在又嫁人,是这样的状态。 后来A的女儿知道这件事,就哭着对她外公说,你不公平,你对我舅舅怎样,对我妈又怎样?要不是你,我妈也不至于这样。 2021年4月7日,南京郊区农村池塘边洗衣服的村民妇女。图片:视觉中国 全现在:像你在论文里提到的这些关系,比如婆媳关系、女儿和娘家的关系、亲子关系等,这些年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呢? 宓淑贤:先讲婆媳关系吧。在调研的过程中,我有点同情我父母这一代的女性。像我们村子,在苏北,靠近山东,在江苏相对来说经济比较落后。我们这里的家庭,子女比较多。我妈妈这一辈的女性年轻时,平时要干农活,孩子就没有人照看,所以和婆婆的关系不太好。我访谈的大部分人,都在控诉以前婆婆是怎么对她的。 其实这里的矛盾在哪里呢?我奶奶那一辈人的婆婆,也是多子女家庭,子女比下一代人更多。比如,等到她大儿子结婚之后,其他的儿子们还没有结婚。她就要继续挣钱给他们娶媳妇,所以她不太可能帮大儿子家带孩子或者干活。但是对大儿子来说,他结婚之后也生了几个孩子,他就会说,如果你不帮我带孩子的话,我就没法挣钱,没法生活。 对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来说,他们的观念就是,长兄或者长姐,要为弟弟妹妹在经济上付出。这时候,经济上的矛盾会引发情感上的矛盾。所以吵架、打架的人特别多。 而对于新生代的农村居民来说,虽然也是多子女,但最多也就是两个三个。村子里上一代的分家,因为孩子太多,所以是经济上彻底切断。这个“彻底”是说,儿子结婚之后,基本不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了。现在都是“假分家”,就是说,儿子挣的钱儿子花,老子挣的钱还是儿子花,但儿子挣的钱老子就只能看着。在一种传统观念里面,老人所有经济上的东西,都要留给儿子。 我父母这一代的女性,年轻的时候和婆婆关系比较差,甚至恶语相向。但现在她们自己做了婆婆后,是要“巴结”儿媳妇的。因为农村里的大龄剩男太多了,能结婚已经很不容易。“光棍”在农村里是尴尬的,不仅自己会被指指点点,连带着别人也会认为你父母没有能力。这种情况下,婆婆是不敢和儿媳妇起冲突的。这一代就变成了媳妇当家,什么事情都要顺着媳妇的心意。 生育方式也有些变化。以前村里把剖腹产妖魔化,现在又是另外一个极端——谣传剖腹产特别好。村里的人说,10个有8个剖腹产的。 恩报系统运作下的亲情 全现在:以往研究农村家庭关系的学者,是如何在民族志中探讨这些话题的? 宓淑贤:比如说杨懋春(中国社会学家,其著作《一个中国村庄:山东台头》是乡村社会学的经典作品)的研究,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生活,以山东一个村庄为样本。因为我的田野点靠近山东,所以我有关注他的研究。他的作品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父母和女儿的关系,比如提到父母和女儿只有在女儿嫁出去之后才会有推心置腹的交谈。也有讲父亲和女儿之间会有意回避,以及婆媳的矛盾。 而费孝通讲过的是,怎么给儿子找童养媳,当然他是从乡村经济现状考虑的。阎云翔也会讲,但他侧重的是情感,是母女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其实这些话题一直在讲,只不过主题不太一样。 2007年2月24日,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某农村,一户农家正在用手扶拖拉机装运棉花杆。图片:视觉中国 全现在:你是如何从田野发现中,总结出最后的结论的? 宓淑贤:我做田野的时候也有发布一些相关的论文,和博论的问题意识有一些区别,但实际上都是博论的延伸。比如我2019年发表的一篇《新时期的“婆家”和“娘家”:性别比例失衡下的压力转移》。前期好多人的研究会认为彩礼是父母剥夺女儿、兄弟剥夺姐妹。但我的结论是,整个农村社会,这种压力其实是在转移的。一个女性既是女儿又是儿媳,在彩礼这件事上被自己娘家剥夺的同时,也在剥夺婆家。整个村落都是一种被剥夺的状态,过得比较辛苦。这种辛苦的生活,一定原因也在于男女比例失衡。 女性在娘家,其实是处于经济被剥夺的状态。在婆家,她又处于家庭的中心。这其中似乎很矛盾,因为在娘家和在婆家的状态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在访谈中,这些女性还是会认为娘家对她特别好,而婆婆会怎样怎样。为什么新生代农村女性在娘家是这样一种状态?我认识这是一种恩报系统。 以往研究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学者,讲恩报系统的时候,更多是陌生人之间、朋友之间。我是觉得这可以放在家庭之中。因为我在调研之中,频繁听到女性说,父母养育了我,那他们把钱拿走给弟弟又怎么样,那也是我的弟弟。 所以,“亲情”这个抽象的概念,在人的行动、决策之中,在女儿和娘家的关系上,就是通过恩报系统来运作的。父母家庭、周边的乡土社会,都在告诉女性说,如果说你长大了,你嫁人了,你是要给娘家做贡献的。在乡土社会里,在经济上补贴父母,是会被褒奖的。孝道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,被人夸孝顺,也会对人的心理状态影响很大。这其中也有一种激励的关系。 而这个恩报系统,也在影响女性后续对娘家和婆家的关系。我自己提出了一个概念,叫“亲情感”。我觉得我们可能也可以用一种偏量化的方式去谈论亲情。在女性的不同年龄阶段、不同角色之中,“亲情感”是对女性有不同影响的。 全现在:你的田野点同时也是你的家乡,你觉得你自己的人生经历,对你的研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? 宓淑贤:虽然我把新生代女性作为一个群体,她们有一些共性,但是实际上你发现即使同样一种行为,她的主观感受、导向也是千差万别。 新生代农村女性和我的成长经历之间,其实有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存在。我去田野点访谈的时候,会问,我小时候是这样的,你也是吗?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找到共鸣,从而把这件事推进下去。 2019年11月19日,江苏连云港,赣榆区塔山镇一家玩具厂里,当地农村妇女正在生产车间里加工玩具。图片:视觉中国 全现在:现在你还有哪些想做的研究是和农村相关的? 宓淑贤:我现在进行的研究也是我从田野中发现的一些东西。比如说关于养老,我看到农村地区有很多丧偶的老年妇女,她们之间兴起了一种新的养老方式,就是搭伴养老。 还有就是,人们从农村到城市生活之后,老家的父母过去带娃,但其实主要是奶奶带,而爷爷很少。这其中就会有一些男性,在妻子去外地看娃时,在家里嫖娼,或者出轨。与此相关的,还有中老年夫妇的长期分居,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居,而是因为给不同的孩子看娃。比如夫妻一个给大儿子看娃,一个给二儿子看娃,如果两个孩子在不同城市,就需要分居。像我们那边有一对夫妻长达十年没有见面。这种去外地看娃的中老年人,在城市里生活,慢慢融入进去之后,会把家乡的一些东西带到当地。这个我也想做一些研究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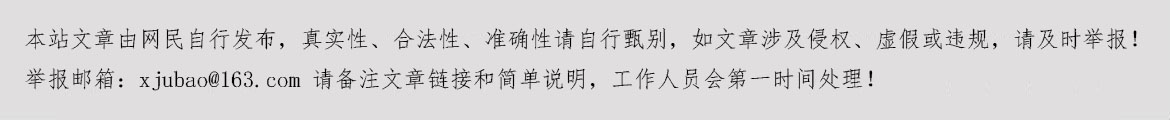
|